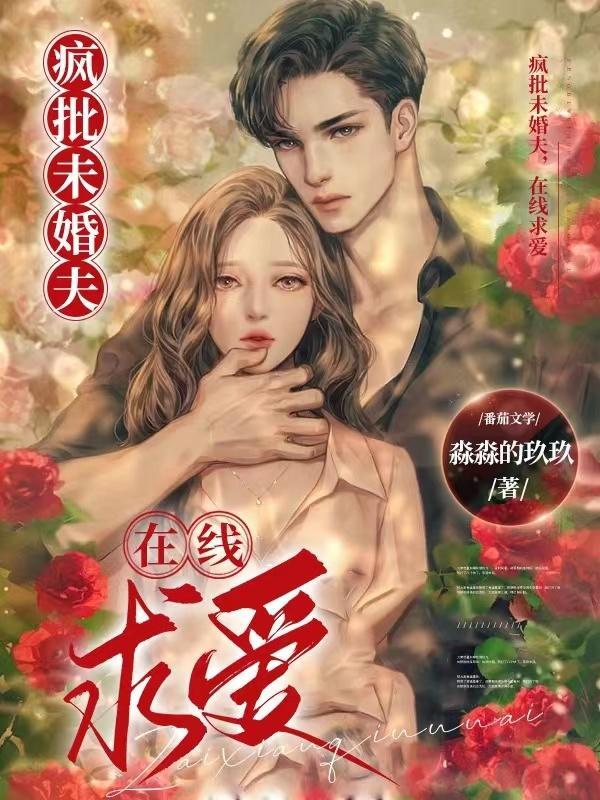宜小说>快穿:谁说软妹要听话!bu! > 第535章 伤痛文学中的小青梅22(第3页)
第535章 伤痛文学中的小青梅22(第3页)
顾楠一副做错事的模样,我跟这个弟弟也没什么好说的,把他送回去就独自回了自己房子。
詹清怀出差是常事,但没想到这次居然遇到了危险。
外省大雪,交通瘫痪,他被困在了酒店。
当我不断打电话去律所询问,对方不耐烦告诉我詹清怀和许律师暂时回不来后,我感觉天都塌了。
他们一起出的差。
我哆嗦着给詹清怀打电话,对方不接。
一星期后,他们才顺利回京市。
詹清怀难得踏进了家门,只是一进门就拉住我的手,求我离婚。
“你们生关系了吗?”我嗓子哑的不行,一说话就疼。
詹清怀否认,我不信。
我不说话了,回主卧反锁房门,从柜子里拿出詹清怀刮胡子用的刀片。
我也学着电视剧里那样,钻进浴室,一刀刀去划自己手腕。
可是死真难,我怕疼,不敢用力,就更折磨自己。
我找不到位置,这种锐痛让我丧失了理智,忍不住就尖叫了一声。
最后失血过多,我晕了。
再醒来时,身边围了好多人。
干妈见到我醒了,扑过来抱住我哭个不停,秦阿姨也在流泪。
爸爸可能是气坏了,冲过来想打我,但是被干爸拦住了。
我艰难地把视线移到詹清怀脸上,他脸上都伤,谁打的?
长辈们把空间留给了我们,詹清怀第一次抱住我,他说不离婚了。
我却没有想象中高兴。
养伤这段时日,詹清怀成了二十四孝好丈夫,每天回家,还会做饭给我吃。
可我看到他那阴郁又沧桑的脸,心里就绞痛。
明明不愿意,干什么要装成在乎我的模样?
我开始找茬,像个疯子一样折磨他也折磨自己。
詹清怀和许珺焰在酒店待的那七天,成了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真的受不了。
吵着吵着,又变成了从前的样子,只是詹清怀不敢把我自己放在家里。
伤好后,我们也静下心谈过。
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又不是什么法律法规,没有原则可讲的。
那天下雨,我叠完阳台上的衣服,从玻璃倒影上,看到詹清怀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