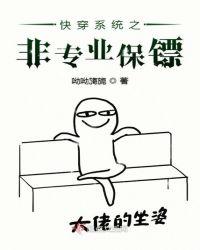宜小说>痞子,你给我站住! > 第156章 屋子太小放不下(第2页)
第156章 屋子太小放不下(第2页)
浅藏的一个隐秘。
凌书墨早前查过许多线索,如今只能静静地看着他,眼神中显露无尽关切和黯然。
骄傲自负如这个人,一直不愿意说出来,大概就是只想自己承担。
他一直等着这人能够说出口,不说就真的不问。
“这幅画被先帝当场焚毁。”陈形意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传闻中明明……”
“呵!”白豌笑了,语气中依旧是那般无可奈何。
就是这个语气。所有人都不信,告诉他们画早就没了。
凌书墨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这人强颜欢笑的模样,却是第一次见到这人姿容冷色到如此不同以往。
“六年前,我是亲眼见到先帝把画撕毁,丢进火盆之中毁了的……”
那幅他踏遍大江南北,呕心沥血的冒死之作。
白豌指尖的水渍逐渐消散,如今已经成了一个冤孽而已。
“也不知道谁说的,那幅画有罢黜百官之能。这种荒谬的话,怎么会有人信呢?”
是啊,怎么会有人信呢!
先帝贤明,遇到他这般天真无知的举动都免去了死刑。
可自己好不容易从刑狱司离开,却成了坐井观天之人。
陈形意倒抽了一口冷气,顿时欲言又止。
如果一个月内拿不到这幅画,那么就得杀了毫无用处的韩妙染。
“老大,就没有小样或者画坏的图纸之类吗?相关之下,不可能什么都没有!”他忧心问道。
白豌面沉如水,似乎有些思绪万千的闭眼。
一旁的凌书墨这才欠着声音:“当年韩府所有的画一夜之间消失,所有家仆或消失,或病逝。”
如果说,先帝想要人和他的画从这个世界消失。那么就还有人为了荒谬的理由,想要得到那幅画。
“六年前,他们都不信。你觉得,六年后就会信吗?”白豌叹息了一句。
尽管,他如今是盲的,看不出更多情绪。
可是,以凌书墨对其多年的了解,绝对能现这人如今该是戏谑中带着点无奈的。
“老大,若是没有这幅画。你会……”陈形意接下来的话没有说下去。
既然他找的到,那主上其他的死士也是找的到这里。
其他人,可不会像自己这般念着兄弟情义不动手的。
白豌不屑:“直接点,会死。不过我看上去是那种随便被人摆布的人吗?”
六年前,他逃得出来。六年后,也可以。
大概吧……
陈形意心中苦笑,这可不是摆布的问题。
其后夜深人静,竹林小筑之间,三人实在无法入梦,似乎都藏着些各自心思。
“子辰,我们让陈二睡外面,是不是不太厚道?”
白豌就算自认为厚颜无耻,也没有把自家兄弟放去门口长椅睡的。
“屋里没有多余的床。”凌书墨幽幽道。
白豌稍稍整理了下床榻叠被。屋内一张竹床,一个软榻,他们一直也就那么睡。
“其实,也可以让他把长椅放进来。我们一人一张,或者两个人互相挤挤也没什么。”
黑夜中原本温润的人,难得语气执拗和强硬。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