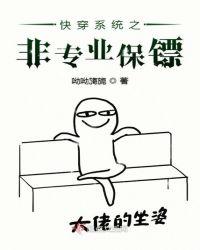宜小说>南明谍影 > 第895章 明察暗访白马镇十一(第1页)
第895章 明察暗访白马镇十一(第1页)
“人不可貌相呐!”唐世勋好奇地问道:“莫非,黄婆与赵家有甚亲戚关系?”
老郑头摇道:“应当没甚亲戚关系,黄婆一家是去年从长沙府逃难过来的。”
“长沙府的?”唐世勋若有所思地摩挲着下巴:“在下见那黄婆在路上与一些相熟的妇人闲聊,似乎也看不出她有多精明,再有。”
唐世勋剑眉微皱:“按理说黄婆作为宝庆府分会商贸投资处的副司长,单是薪俸就已不低,若有商人请她审批投资又岂会少得了好处?为何她不像郑老伯您这般花上三十两银子买座巷口的宅屋?”
“章公子所言甚是,黄婆捞银子的法子应当不少,但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她们一家四口的开销可不小呐……”
老郑头一声轻叹解释道,黄婆的老伴梁伯就是个药罐子,那身子骨也不知还能挨多久。
据说梁伯好几次想要寻短见,但都被他的孙女婿给阻止了,而这孙女婿又是残疾,同样得花银子治。
偏偏这孙女婿还在家舞文弄墨,这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而黄婆的孙女儿又是个哑巴,平常在家照顾爷爷与丈夫就已是不易,自然也没法出去找别的活计。
因此黄婆即便能赚不少银子,但她哪能一次性拿出三十两银子来买断宅屋?
唐世勋敏锐地听出老郑头话中的一个关键点,他不禁笑问:“这一家子倒是稀奇,梁老爷子不愿拖累家人欲寻短见,孙女婿竟能劝得住?可这孙女婿虽有残疾,但既然能舞文弄墨又为何不想法子贴补家用?却忍心让跛脚的黄婆一个人在外辛苦?”
“可不是嘛!”老郑头拍了拍腿,语气不满地说道:“因此街坊邻居们才说黄婆的孙女婿龙先生性情古怪咧!他不过是断了左手,用右手不也能书写?去当个书吏总归能有些收入不是?可他就像个娘们似的躲在家中甚少出门。”
随即老郑头又苦笑道,但黄婆对这孙女婿龙先生可是心疼得很,记得前几日的一个傍晚,龙先生在巷中散步,黄婆竟是和她孙女儿陪在他两侧,就好像生怕他不慎摔倒似的。
“章公子您说谁家老人会如此‘供’着孙女婿?”老郑头吹胡子瞪眼道:“若老夫的孙女儿以后找个这等夫婿,那老夫不得被活活气死了去?”
唐世勋目光幽幽地看着天井问道:“郑老伯,赵攸公子可有来过黄婆家?”
老郑头摇失笑:“赵攸公子可是大忙人,他哪有这等闲心咧?”
随即老郑头搓着双手笑问:“章公子,不知您来白马镇做何买卖?可否需要老夫帮您去跟黄婆说道说道?”
唐世勋如何不知老郑头那双眼睛一直盯着他手边的金子?他淡然笑道:“在下有精盐数千斤,不知黄婆可有法子运去关外两里集卖个好价钱?”
“精盐?数千斤”老郑头险些从竹椅上跳将起来:“章公子此话当真?”
“骗你做甚?”唐世勋故作不快地睨了他一眼。
老郑头皱眉道:“公子,老夫晓得关外两里集的买卖比白马镇还好做,但精盐在镇上都是紧俏货,何须冒险运出关去咧?”
“老伯您有所不知……”唐世勋一脸自信地解释道,如今衡阳城东郊已在勘探岩盐,虽说离开采还需不少时日,但那片岩盐怕是能开采上百年乃至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