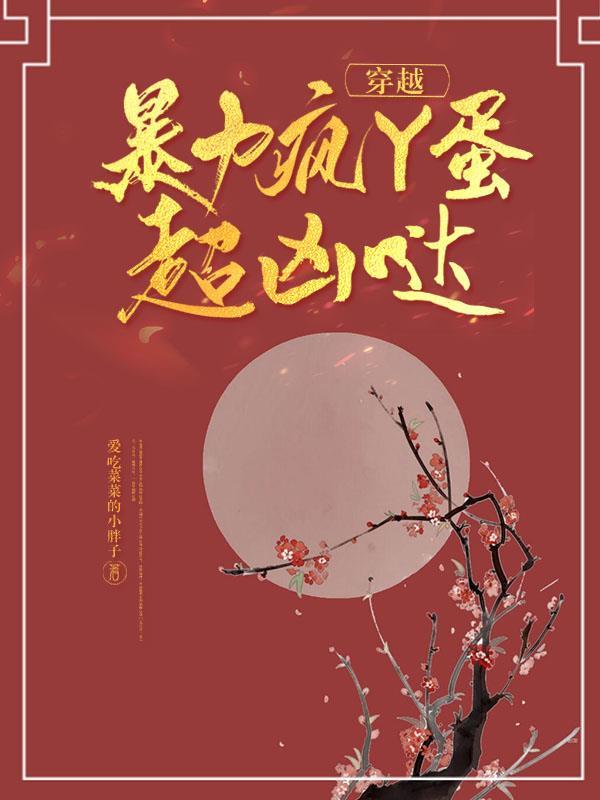宜小说>间歇热恋 > 第20章(第2页)
第20章(第2页)
阮院长是个丁克,阮青屿从小就被他当半个儿子疼着;最近阮青屿车祸后脑子偶尔犯糊涂,一声二叔,他便召唤兽一样随叫随到。
十分钟后,阮院长出现在阮青屿房间的庭院里,看着自家国宝酒气冲天地坐在木台阶上呆。
“阮螃蟹,你这是爬不动,还是脑子挂了?”阮院长问:“要我背你吗?”
“懒得爬。”阮青屿回答,虽然自己嘴上资本家资本家喊着阮院长,但自己作为阮家独苗,在家里是霸主般存在。
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才是阮家最大的资本家,剥削型资本家。
“凌泽那小子又欺负你了?”阮院长蹲在他面前问道:“我还想这么多年过去,他能靠谱点呢,又把你怎么了?姓刘的没有替我灌死他吗?”
阮院长一副气不过的样子,伺候业主归伺候业主,但是他对凌泽一贯带着偏见。阮青屿大二时,他就要抓人进设计院,但是当时阮青屿只肯跟着凌泽,说什么也不肯提前实习,也只能作罢。
那个凌泽,只会耽误自己家小孩。
“哪个姓刘的?刘局吗?”阮青屿听着阮院长的口气,跟在喊马仔似的。
“对啊,他没和你说吗,他我大学同学,当年高数要不是我让他抄我卷子,他都毕业不了,还当什么局长,失业局局长。”
“你怎么不早说。”阮青屿的委屈已经不是用愤怒可以化解了,要知道这刘局是阮院长的马仔兄弟,刚刚从卫生间出来,他就直接装死回房间,还应酬个什么劲。
“我就交代他灌死凌泽,哪里知道你会在啊。”阮院长振振有词。
阮青屿哀嚎一声,把阮院长推出院门,让他回大堂吧打掼蛋,别再来烦自己。
庭院重新恢复宁静。
阮青屿又站在院里,盯着二层小楼看半天,底层竟有扇门可以直通庭院。他按下对讲机,找桑吉。
对讲频道里挺热闹,正通知开会什么的,阮青屿试着联系桑吉,说需要多床羽绒被。
桑吉应答得很快,没几分钟便开着电瓶车运着羽绒被,滴滴滴地停在院前;他抱着被子箭步跑上二楼,哐哐敲着门:“阮工,阮工。”
桑吉每次出现都是阮工,阮工地叫得热情洋溢,阮青屿的心情顿时被他喊得好了大半。
“阮工在楼下。”阮青屿从木楼梯的阴影里笑着走出来:“你进房间,下底楼,把底楼通向院子的房门打开。”
阮青屿是铁了心的不上二楼,他不想再为了上个卫生间翻山越岭,所以今天他决定让桑吉在底楼给自己铺个地铺,顺带自己的行李也搬到楼下来。
“阮工想睡地板?”桑吉语气惊讶。
“嗯,不想爬楼梯。”阮青屿回答。
“那我把被子给你铺浴缸里?总比睡地上强,一楼潮湿着呢。”桑吉道。
很快浴缸地铺便打好,羽绒被铺了一层又一层,卧室的枕头也都被搬下来叠放着,看着很不错;与桑吉道谢后,阮青屿欢天喜地地躺下,横竖还挺合适。
浴缸正对着窗,是橡木桶状,又高又大,能容下两个成人,四周围着圈卵石,上几步木台阶才能躺进来。
阮青屿起身,爬出浴缸,推开正对浴缸的观景窗,窗户正对着草场,远处重峦叠嶂,月色无边。
而躺在浴缸里,恰好可以看到那轮银盈月。
阮青屿很满意,正陶醉着,脚一滑,直直摔进浴缸里,砰一声,昨天在路虎车上被磕的位置,恰巧又狠狠撞在浴缸沿上。
他眼冒金星,鼻子酸,亏得浴缸里已经铺了被褥,他便脸朝下,顺势趴在柔软被褥上缓了缓。
脸埋被子里时间太长,呼吸憋闷,所以,阮青屿决定开个窗。
他一翻身,盈月正温柔地看着自己,大而模糊,泛着乳黄棱光。
窗户是被打开的。
阮青屿顺起自己的记忆,酒局,香菜汁,路虎的a柱,阮院长被推出院子,独克宗古城夜景,凌泽的黑蓝丝巾……
美好与疲惫交织着,混成一团。
![福猪小团子五岁啦[七零]](/img/6612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