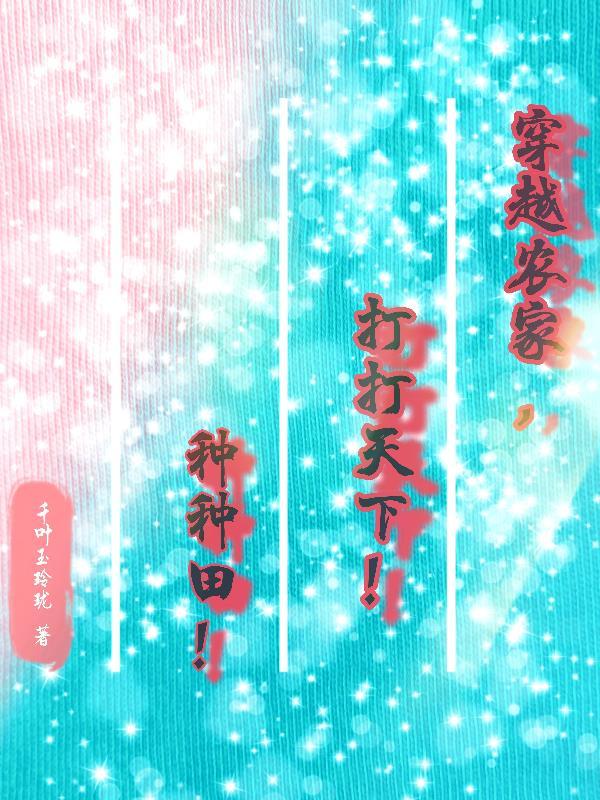宜小说>醉金盏 > 第201章 但您当真没有一点疑惑吗(第3页)
第201章 但您当真没有一点疑惑吗(第3页)
与其说是五皇子妃的事,归根结底,是那把椅子的事。
太大了,我们不能随意掺和。”
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但当夕阳西落,下了学堂的孙儿孙女结伴来向她请安时,敬文伯夫人的嗓子干涩得厉害。
周沅有两位兄长,他们各自都有了儿女。
敬文伯府不需要周沅承担家业,周家的枝叶不说多么繁盛,但都长得不错。
可是、可是若没有当年那些意外,现在她的身边也会围着属于阿沅的孩子啊!
这种念头一涌上来,敬文伯夫人就很难平静,夜里辗转反侧。
敬文伯已经知道状况了,见她睡不好,劝道:“别想了,儿孙自有儿孙福。”
“可我当真、当真想要问问为什么。”敬文伯夫人哽咽着道。
“私底下说得好好的,忠勤伯夫人上门保媒时却突然反悔了,甚至连寻的由头都可笑得要命。”
“好在人家忠勤伯夫人心善,不计较丢了颜面。”
“阿薇丫头今儿说错了一桩事,我从第二位就精挑细选,旁的都能将就,就身体康健这一条绝对不能将就。”
“那姑娘个头不高,但打小跟着她父亲练武,一拳头砸树上、能砸下来三四个果子,一年到头都不生病,结果却……”
敬文伯坐起身来,夫妻多年,他知她心结。
他道:“不该和阿娴定亲的。”
阿娴就是敬文伯夫人的内侄女。
“怪我病急乱投医。”敬文伯夫人的眼眶在黑夜里通红一片。
接连“克”死两位,周沅说亲自然有困难,甚至还有人弯着绕着让她放弃小儿子。
敬文伯夫人彼时“年轻气盛”,一心要为儿子洗脱“罪名”,回娘家去商量了一番,定下了侄女儿。
亲上加亲,且知根知底。
阿娴人不如其名,闹起来爬树上房,能耐得很。
可就是这么能耐的野姑娘,小定后也病倒了,没多久……
嫂嫂在白事上几乎哭得厥过去,冲上来要和她拼命,一遍遍喊着“我当时就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
父母兄长都没有为难她,可她内疚啊!
再相信自己的儿子不“克妻”,面对着白绸白蜡烛,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后来,不止是阿沅心灰意冷了,连敬文伯夫人自己也冷了。
京中风言风语越来越重,尤其是文寿伯府和应聆那“异军突起”的好名声,显得他们周家可笑又可恶。
“一连克三个,难说不是报应。”
“他家善堂是不是有问题?定是亏心事做多了,才会办善堂。”
“可怜人家好姑娘,全被害了。”
“哎,命不够硬,挡不住煞,文寿伯府就厉害了……”
“难道不管不顾要反悔,原来如此,他家小五是个有福气的。”
“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命。”
“是了,好像还有高僧批了命是吧?”
明明已经那么多年了,可那些流言蜚语缠绕在敬文伯夫人耳边,仿佛昨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