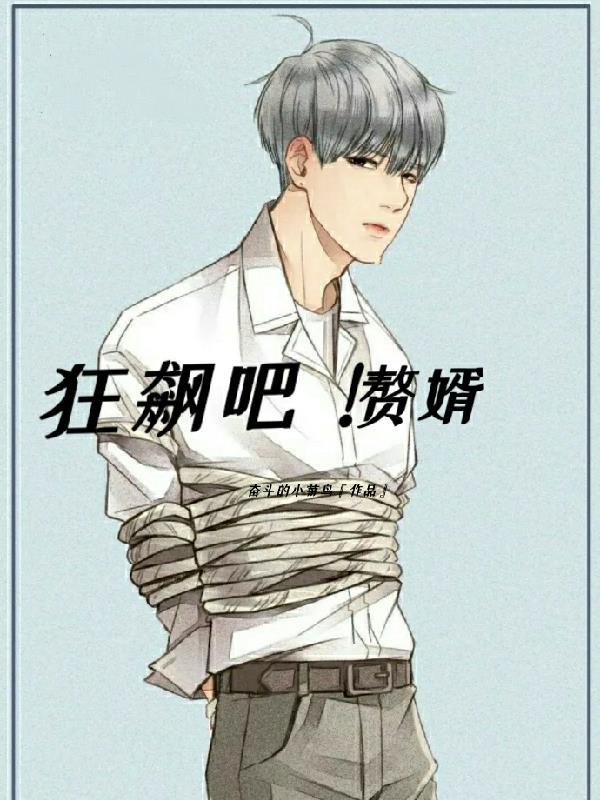宜小说>家父万历爷 > 第357章 兵围香山澳(第2页)
第357章 兵围香山澳(第2页)
那范涞倒是比张鸣冈淡定些许,闻言回道,“军门勿急,下官已差人就近征调船只去了。”
“怎能不急?”张鸣冈跺脚道,“殿下万金之躯,你我担待不起!”
看老头呼吸不畅,左右摇摆,范涞急忙上前搀扶,嘴上说道,“军门可曾见过瀛州炮舰?”
“不曾,所言何意?”
范涞淡淡一笑,“下官在粤多年,曾亲眼得见葡夷战船巨炮,此所以葡夷难治,不服王化也。然则瀛州水师战船更利,于外海巡逻往复,战则无往不利,诸夷不敢争锋,此所以才有我广东沿海安定,不见夷船寻衅地方。是以下官推测,葡夷未必敢于同瀛州水师争锋。再者,下官虽从未得见殿下,但以殿下治理瀛州,市舶福建等等传闻,可见殿下行事心思缜密,谋划高远,是以下官斗胆推测,殿下未必当真要开战,而是别有他意。”
“但愿如此!”张鸣冈颤声道,“虽如此,你我还是要尽快赶往香山澳,如今两广多事,这沿海不能乱啊。”
市舶司所在,自然船舶极多,众人议论间,两艘被强征来的商船缓缓靠岸,官员一窝蜂登船,驶向外海。
谋划筹备月余,朱常瀛终于收拾包袱,前来广东赴任,只是排场有些吓人,瀛州本部战舰12艘,各地抽调快巡船25艘。
舰队浩荡,不可一世。
要干啥,自然要强势接管香山澳,堵住大明海外走私最后一个缺口。
而市舶司选址,自然也在这里,市政、港口、街道。。。。。。葡人在这里偷偷摸摸经营几十年,底子很好,不拿来用不是傻子么。
再者,淡马锡军港的设立,使葡人傲娇而脆弱的神经濒于崩溃,矛盾似乎已经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西洋商行船只在南印度遭袭次数持续增加,虽没有证据,但朱常瀛把这口锅扣到了葡人头上。
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么主谋就一定是你。
顺着这样的逻辑,那么香山澳的贸易继续由葡人把持也就没有必要了,而筹建市舶司,便是拿到香山澳控制权的契机。
至于为何搞突然袭击?
一是担心葡人转移财产,搞破坏。事实上香山澳的葡人一直在向马六甲,甚至马尼拉输血,这令朱常瀛如吃了苍蝇一般难受。
二是怕广东官员阻挠。不管什么东林党、楚党、浙党之类的,朱常瀛统统把他们归类为保守派,而以自己为的瀛州一系,相对应的就属激进派。指望着保守派能理解并支持激进派的革新举措,简直比不让狗吃屎都难。这是朱常瀛在鼓浪屿面对福建百官总结出来的血泪教训,与其浪费时间讲道理去争取,不如摆出事实强迫他们来接受。
指挥室里,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落在一身戎装的挺拔身躯上,戎装庄严华彩,金丝银线闪烁着异样光芒,高贵而威严。
朱常瀛面如止水,平静的看向几位葡人使者。
“几位,有关设立市舶司之后葡人的待遇,你们也看了,如何抉择?”
“殿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贵国圣人的名言,我葡人也怀有同样的朴素情怀,上帝见证,在香山澳定居的葡人对大明绝对没有恶意。同时,我们之间的交往同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殿下突然对远方来的朋友武力胁迫,逼迫他们放弃应有的权利同财产,离开香山澳。
伟大而仁慈的瀛王殿下,如果您的子民在海外受到这样的欺压,您会容忍么?如果您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会甘心放弃而离开么?
我请求您,请给我们说话的机会,以彰显您的宽容同慈悲。”
朱常瀛抬眼看向这位穿着朴素的欧罗巴老传教士,淡淡一笑。
“ninetgobardi,汉名龙华民,在我大明传道多年,交友广阔,利玛窦居士去世以后,由你接任耶稣会中华省会长,执掌传教事业,立志使我大明子民沐浴在主的光辉之下,得享主的恩惠。
你是传教士,隶属于教会而非葡人。
那么孤王有一个疑问,你究竟代表谁的利益而来?”
龙华民神情微动,转而释然,“世间的一切,皆遵循主的指引,我是为了和平而来。”
“也就是公平公正,没有私心?”
“是的。”
“那好,孤王问你,香山澳是谁的国土?”
“大明,但以每年5oo两地租租给了葡萄利亚国。”
“那好,我大明不租了,可有问题?”朱常瀛冷冷笑道,“又或者,龙居士可以代替葡萄利亚国做出决定,在葡国本土也租赁一块这般大小的土地于我大明,由我大明自行管理?
若能如此,孤王不介意同你签订一份租赁契约!”
龙华民默然站立,沉默良久,摇头道,“我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