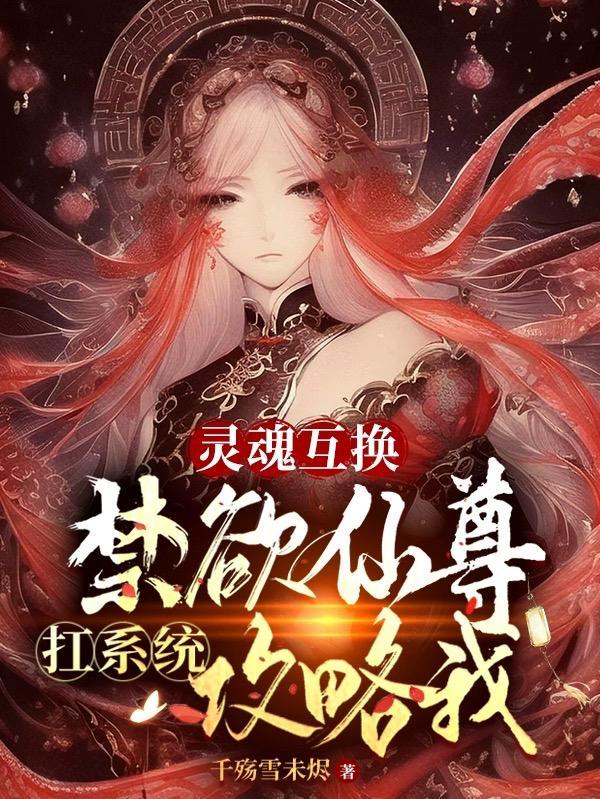宜小说>间歇热恋 > 第26章(第2页)
第26章(第2页)
而自己早上还睡在南洋别墅的空调房里,晚上便只身睡在异国他乡的木舢板上,每天在不同的渔船里躲藏。
饶是这样,却还是被债主找到,在揍一顿被脱光后,丢在码头冻鱼的冷库里,录着视频,给凌泽父亲,威胁要钱。
当凌泽在黑暗的冷库里,冻得神志游离时,唯一想到的人只有阮青屿。
他很遗憾,自己从来没有好好抱过阮青屿,也不曾向他吐露过自己的心迹,冷库外的太阳是什么样子,也许是再也见不到了,如果有下辈子,希望自己可以再遇到阮青屿。
幸运的是,不需要下辈子,现在阮青屿便温顺地被自己拥在怀里,像是自己凄寒经历中永不凋零的温柔日光。
“阿屿,我真的好想你。”
**
当阮青屿坐回路虎副驾时,他又开始庆幸,自己高反严重的毛病,可真是来得恰到好处,他可以随时随地按需装死。
比如现在,他举着氧气瓶,滋滋吸着,塑料氧气面罩,遮住他大半张脸,这样凌泽就不会注意到自己烫得红的脸。
“阿屿,你脸上的氧气瓶已经没有气了。”凌泽边开车边说。
“还有点,不要浪费。”阮青屿觉得现在还不太适合把氧气罩从自己的脸上挪开,毕竟自己感觉脸还是有点烫。
“车子远光灯的光线,是往前直射的,阮青屿,你脸再红我都看不见。”凌泽边说边加着。
阮青屿听他这么说人都要气炸了,一怒,把氧气瓶咣当丢向后座。
“啧,是有什么好脸红的,是你缠着我,又不是我缠你。你再消遣我,我下车了啊。”
“你下车,是要猴年马月才能走到民宿。”凌泽说:“看下导航,大概是还要再开多远。”
“哦,你等下。”
阮工的七日度假游,在第四天晚上,插入段小插曲,h酒管集团董事会成员凌泽,在向阮工诉衷肠后,耍赖皮,抱着人不肯松手。
当时,阮青屿说天快全黑了,得赶紧走;他用力去掰凌泽的手臂,却一点用都没有,那双手臂就跟铁铸一样焊在自己身上。看来练家子的不止周成资一个人,凌泽也是和他一伙的。
两人就这么在服务区角落里折腾着,一个挣扎着要走,一个说黏住了拔不开,打得不可开交,反正月黑风高的,也没人看得清。
直到酒店阿尔法的前车灯,落在两人身上。
两人就像夜晚沙滩上,被强光照到后的螃蟹似的,一动不动。
阮青屿双手正力把凌泽的左前臂从身上掰离,一只脚还踩在凌泽的鞋上;而凌泽则是一手被阮青屿掰得动弹不得,但另一只手却钳在阮青屿腰上,阮青屿也一样动弹不得。
林晓培坐在副驾驶,笑得不行,说这两人打架呢,大高原的海拔38oo,别打着打着晕过去了啊。
而下车的教训两人的是阮院长,他直接走向阮青屿,抬起手就要往后脑勺扇去,幸的凌泽反应快,一把抓住阮院长的手臂:“阮院长,别打,万一把他脑子打宕机怎么办。”
“你们开车这个度,和宕机有区别吗?”阮院长收回手:“我们都看完场地回程了,你俩还在这里打架。”
阮院长对阮青屿,工作和生活完全是两个态度,工作稍微拖拉点就伸手要揍人,而生活上却是买蟹老板气球哄小孩的样子。
“晚上都不准回酒店,明天一早给我看完场地再回去。真的是胡作非为。”阮院长骂道,连带凌泽一起。
“不回酒店,那晚上睡哪呀?”阮青屿问。
“路边民宿随便找一个。明天天一亮就去看,看完马上开车回酒店。”阮院长命令道。
“哦,好。”阮青屿老老实实地接受批评。
新酒店的选址,在当地最高雪山附近,具体位置还没定,二选一,所以需要到现场踏勘,以确定出合理的方案。
阮青屿想着,既然天一亮就要返程,那就选个离现场最近的民宿算了。待到导航路线一出,两人都傻了眼,直线距离1o公里出头,却要在山路十八弯上,弯弯绕绕地转上3o公里。
但都已经定了,便硬着头皮开了过去。
等到开到民宿门口,已经是晚上接近午夜。

![八爷在清穿文里割韭菜[共享空间]](/img/101251.jpg)